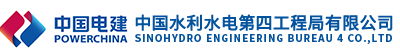【品牌采風】臨高而立,云端筑夢 |
|
|
|
|
晨霧如紗,纏繞在秦嶺北麓的千仞絕壁之間。我們隨著東莊施工局的皮卡車顛簸著駛向涇河峽谷。車窗外的秦嶺在薄紗中若隱若現,那些被歲月打磨得溫潤的峰巒,此刻正以一種近乎神圣的姿態矗立著。 我站在東莊水利樞紐的施工平臺上抬頭仰望——山,是沉默的巨人,以鐵青色的巖脊割開黎明的天光。它們太高了,高得讓飛鳥遲疑、流云徘徊,讓站在其下的人,不由地生出一種渺小之感。這是陜西涇河峽谷的蒼茫之境,山高水長,天地幽深。 沿著鐵架的樓梯向上攀爬,混凝土的氣息逐漸被山風稀釋。當雙腳終于踏上壩頂,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“高”的第二種定義。那不是山岳的高聳、亦非天空的遼遠,而是人的意志所壘砌的高度,一種莊嚴的、近乎神圣的巍峨。 腳下,是新澆筑的混凝土大壩。它表面平整如巨鏡,在晨光中泛出青灰色的光澤。我向前走了幾步,扶欄低頭——一瞬間,呼吸屏住了。河谷在腳下縱深劈開,涇河如一道細瘦的銀鏈,在百米之下隱約閃爍。曾經轟鳴的挖掘機、載重卡車,如今望去如兒童散落的玩具;施工道路上移動的安全帽,成了模糊的色點。風從谷底逆沖而上,掠過耳畔,已帶上了幾分野性與寒意。這是一種脫離了大地庇護、懸立于虛空之上的高。它不靠天賦地脈,而是由四局建設者的雙手,一倉一倉、一罐一罐,澆筑起來的垂直的奇跡。 太陽逐漸升高,薄霧散去。午間的陽光毫無保留地傾瀉在這座新生的龐然大物上。混凝土的表面開始反射出有些刺目的白光,壩體結構投下巨大而堅硬的陰影,將整個峽谷割裂成明暗交織的圖景。我沿著壩頂行走,腳下的每一寸,都凝結著無數個日夜的奔忙——測量員的計算、質檢員的堅守、工程師的不眠、安全員的叮嚀。這高,是科技的高度,是協作的高度,更是責任的高度。它高到必須敬畏每一張圖紙、每一次振搗、每一方混凝土的品質。因為這不是雕塑,這是終將攔蓄億萬噸江河、守護萬家燈火的生命線。 就在壩頂一側,一幅巨大的標語迎風展開——“水電四局,筑壩雄師”。它懸掛于山崖之上,背景是裸露的巖壁和蒼茫的天空。在物理意義上,它當然沒有山高,沒有壩高。但在我凝視它的那一刻,卻覺得它才是整個現場——最高的事物。它所懸掛的高度,是一種精神的海拔。那八個字,是宣言,也是史詩。是水電四局團隊走遍千山萬水、壘起座座大壩的鋼鐵勛章。從黃河到金沙江,從劉家峽到白鶴灘,他們把青春壓進基巖,把歲月匯入洪流,把“筑壩”這件事,鍛造成了一種民族驕傲。這高度,是傳承的高度,是使命的高度,是一代又一代四局水利建設者用奉獻和智慧,在神州大地上樹立的精神旗桿。它高過一切物理的極限。風更大了一些,那聲音,像是雄獅的低吼,從峽谷的深處傳來,沉著、磅礴,充滿力量。 我忽然覺得,我所在的不僅僅是一座水利大壩。我正站在一種“力”的上面。這是一種改天換地的力,一種為國筑基的力,一種將自然的險峻化為民生福祉的力。這座大壩終將馴服涇河的暴烈,將滔滔之水化為清泉與電能,流入城鄉、點亮黑夜、灌溉田疇。而賦予這混凝土骨骼以靈魂的,正是那標語所代表的、無數個如同金峰一般平凡而堅韌的四局建設者。 他們沉默如山,卻移動了山河。 他們低調如沙石,卻聚成了高壩。 臨高而立,我心肅然。身后是千峰競秀,腳下是長壩初成,眼前是“雄師”傲視山河。在這座由人的意志所創造的“高山”之上,我觸摸到了這個時代最堅實的脈搏——那不是機器的轟鳴,而是無數顆心臟,為了同一個夢想,沉穩而熱烈跳動的合聲。 離開時,我再次回望。霧已散盡,陽光磅礴。大壩的輪廓清晰地鑲嵌在峽谷之間,如同大地新生的脊梁。而那幅標語,依舊是最醒目的存在。它無需被丈量,因為它所代表的高度,早已刻進時間的長河,必將與這座大壩,與這段奔騰的涇河,與這片四局人奮斗過的土地同在。 |
|
|
|
| 【打印】 【關閉】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