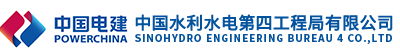【品牌采風】秦陜大地,山河鑄骨 |
|
|
|
|
我向來在風與光的原野上行走,追逐著風機徐徐轉動的翼片和光伏板反射天光的碎金。新能源的工地上,一切是嶄新而輕盈的,仿佛未來已然觸手可及。然而當我立于東莊水利樞紐的壩前,第一次仰視這橫斷山河的巨物時,竟被一種全然不同的力量攫住了——那不是輕盈的飛翔,而是大地的深沉呼吸,是山河鑄成的鐵骨。 這龐然的巨物,如遠古神話中墮入人間的巨龍,僵臥于兩山夾峙之處,將一條奔騰了億萬年的河流攔腰抱住,馴服其野性,卻也激揚其偉力。向來只道風機葉片劃破長空的弧線是時代之詩,光伏陣列鋪展于大地的鱗片是文明之光,它們確然是可敬的。然而此情此景,這混凝土與鋼筋堆疊出的雄渾,卻讓我頓悟何謂“大巧若拙”,何謂“重劍無鋒”。先前的見識,不過是窺見了造化的一角,尚未得睹其全副筋骨。 初到那日,晨霧尚未被機械的轟鳴驅散,我便隨質量管理員老張,開始攀緣這鋼鐵與巖石的叢林。腳下是縱橫交錯的鋼筋,森然如巨獸的肋骨,頭頂是塔吊的鐵臂緩緩移動,劃破灰白的天幕,投下移動的陰影。空氣里飽和著混凝土微濕的腥氣、鋼筋被烈日曬出的鐵腥,還有工人們汗水蒸發出的咸味——這些氣味混雜,竟不使人嫌厭,反倒像土地本身蒸騰出的原始氣息,粗糲而真實,教人莫名生出一種奇異的歸屬感。將掌心貼附于尚存澆注余溫的混凝土上,那微溫透過皮膚,竟讓我錯覺——這沉睡的龐然巨物,是有生命的,它的脈搏正與我自己的悄然共振。 次日,我們再上壩頂。此處離地已有百米,風再無遮擋,野馬般奔騰而來,吹得我衣袂獵獵,幾乎難以立足。然而那些工人卻如履平地,在狹窄的腳手架上,在縱橫的鋼筋骨林間,背負沉重的儀器,手持卷了邊的藍圖,穿梭往來,身形穩定。他們成了這鋼鐵山川之上新的游牧民族,目光所及,非關風景,只鎖定水平尺上那顆脆弱的水泡,只追逐全站儀鏡頭中心那枚細微的十字,只計較混凝土坍落度那幾厘米的差異。我試圖與他們攀談,問詢這宏偉的進程,他們不過抬眼,用被風沙礪得粗糙的嗓音回應三兩句,目光便又膠著于手頭的工作了。原來專注燃燒到了極處,便是這般近乎禪定的沉默,萬物皆褪色,唯余眼前必須完美的方寸。 第三日,我窺見了宏偉敘事之下,最為質樸真實的注腳。時近正午,陽光將鋼筋曬得燙手。一群工人尋了處稍平整的鋼筋叢,蹲踞下來,掏出塑料飯盒。飯食簡單,他們卻吃得匆忙,眼睛時不時仍瞟向攤在一旁、被風吹得簌簌作響的施工詳圖。有人飯粒掉落在圖紙復雜的等高線上,便極小心地用手指拈起,仿佛那線條并非墨水繪制,而是直接銘刻于大地之上的律令,比自家鍋里的米糧更不容輕慢。老張捧著同樣的飯盒,咧嘴一笑:“老弟,別看這一飯一食尋常,咱們手里捧著的,是百年大計,是下游萬畝田、萬家燈火的安穩。錯一分一毫,都愧對天地。”我忽地了然,他們日復一日壘砌的,豈止是千萬方混凝土?他們是在用筋骨和歲月,一鑿一鑿地雕刻著未來的時光,將瞬間澆注成永恒。 我向來篤信,山河乃是造化鬼斧神工的杰作,人力在其上的一切作為,不過是些微末的修補與點綴。而今在這大壩的筋骨血脈間攀爬了四日,肌膚浸染其塵埃,呼吸摻雜其氣息,乃知人亦可以重鑄山河,并非以僭越之心,而是以共生之志。風電光伏,汲取天地之息,固然是可敬的清潔血脈;然則此間橫江立壩的偉岸,卻是另一種氣象——它非是與自然爭一時之短長,而是與之深沉對話,將其億萬年積蓄的磅礴偉力,化作馴服的光明,照亮人間的屋舍與田疇。 離去之時,暮色四合,為巨大的壩體鍍上一層沉郁的青銅色,使其顯出一種近乎神性的、沉默的威嚴。極高處,仍有無數身影在夕照中移動、攀緣、勞作,逆光望去,小如螻蟻,微如塵芥。然而,正是這無數的螻蟻塵芥,以其血肉之軀,竟穩穩地托起了整座新的山河。他們的名姓或許永遠不會被記誦,但他們的生命軌跡,早已被穩穩澆筑在這冰冷的混凝土巨物之中,與之融為一體,成為大地之上一道嶄新的、不可撼動的脊梁。 壩,是工業時代寫給大地的新史詩,是人類意志引發的新一輪地殼運動。而他們——這些沉默的行走者與建造者,便是這史詩的行文,是這運動的核心,是行走于其上的當代造山者。風依舊在遠方的原野上推動葉輪,陽光依舊在更西的戈壁點亮面板,而在這里,水將以另一種形式被喚醒,它的力量不再用于無謂的奔逃,而是納入人類的律動,成為文明脈搏中一股深沉、有力、綿延不絕的節拍。 |
|
|
|
| 【打印】 【關閉】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