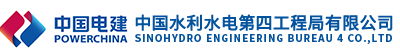高原的風,立秋之后 |
|
|
|
|
立秋的清晨,天色總來得遲疑。西藏的陽光似乎不急于上工,云在山谷里緩緩鋪展,宛如一床巨大的藏式氆氌,將夜的涼意挽留得更久。吉措的風電項目部就坐落在這片高原的風口上,海拔五千米左右,空氣稀薄,連呼吸都帶著喘息。 與內地的工地不同,這里的風是永恒的主人。它自雪山奔襲而來,裹挾冰磧的寒氣、遠處牧場的酥油香,以及峽谷深處湍急河流的水聲。吊車在風中徐徐轉動長長的吊臂,像一只伸展的金屬鶴,穩穩地將葉片托舉向高空。那葉片潔白纖長,尚未與機艙相連,宛如等待合奏的琴弦。 立秋后的吉措,雖褪去了烈日的炙烤,陽光依舊刺目。晨間溫度僅幾度,工人們裹著厚棉服,護目鏡下的眼神被寒氣淬煉得愈發銳利。他們一邊擦拭設備,一邊打著手勢——風聲呼嘯,言語頃刻被卷走,唯有手勢才能精準傳遞指令。 午間的工地稍顯暖意,陽光在鋼結構上跳躍出刺目的白光。焊花飛濺,如同高原天空下綻放的一場微型流星雨。那是工地上獨有的煙火氣,彌漫著鐵與火的味道,與不遠處圣潔的雪山構成奇異對比——冷與熱在同一片蒼穹下共生。 我立于塔基下仰望,塔筒似一根銀灰色的經幡桿,一節節被吊裝攀升,直插云霄。工友阿旺笑著說,這里修的不是塔,是能抓住風的手。阿旺是本地人,平日放牧,閑暇便來工地幫手。他熟稔這片風的脾性——何時會驟然變急,何方更適合吊裝。他說風是活的,時而如朋友,送來清涼與清醒;時而又似頑童,猛地發力,讓人手忙腳亂。 工地食堂雖小,卻熱氣氤氳。午飯多是牦牛肉湯、青稞餅、蘿卜干,簡樸卻蘊含力量。高原的飯食,總帶著一種沉甸甸的暖意,咽下去,仿佛在身上覆了一層厚實的暖土,足以抵御風寒。飯后,年輕的技工常踱到山坡上曬會兒太陽,瞇眼望著遠處的轉經筒隨風旋轉。那一刻,機器的轟鳴與經輪的輕吟交織。 傍晚,立秋的風更添寒意,天邊的云被夕陽浸染成深橙,似被火焰舔舐。遠處的風機已矗立數座,葉片徐徐轉動,像牧人巨大的手掌在空氣中撩撥無形的琴弦。隨風起舞,塔下的陰影長長地鋪展,與山影交融。 這片工地與眾不同,不僅因海拔高、風勁,更因它與自然同頻呼吸。工程進度不單憑計劃表推進,還得看天氣的臉色、風的脾性。落雨便暫緩,風急時必停機,哪怕吊裝僅差最后一環。時間在此并非線性流逝,而是隨季節、風向一同吐納、流動。 夜幕垂落,工地的燈火次第點亮。那光芒在高原的濃夜里格外分明,宛如一顆顆微小的恒星墜落地面。風仍在耳畔呼嘯,此刻卻似乎溫和了些,只輕輕推著流云東行。 我想,幾年后,當這些風機盡數矗立,轉動的葉片將與長空共譜一曲高原長歌。那時,吉措的風不再僅是自由奔跑的孩子,它將化作燈火,化為電流,沿著輸電線路,穿越山谷、河流、城市,抵達千里之外的萬家燈火。 立秋的夜色漸沉,寒氣驟降。我裹緊外套,回望那幾臺已然運轉的風機——它們在風中旋轉,像在為這片土地送上悠長的祝福。 |
|
|
|
| 【打印】 【關閉】 |